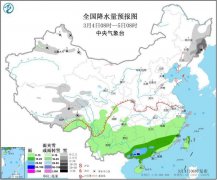计划生育科”里的已婚女性:从“人流”转成了
发布时间:2023-04-03 15:02来源: 未知窗帘是淡粉色的,墙上的科普告示是深粉色的,桌上的注意事项、门口的门牌标识、地上的指引箭头,都是粉色。
三十年来,诊室窗外高楼鳞次栉比,院子里的柳树越长越高,但医院里这间计划生育科的粉色诊室巍然不动,陈素文和科室成了一个锚点,守着一条属于女性的避难船。
在这里,计划生育科医生陈素文接纳着来自不同时代、不同年龄、不同身份、背景、性格、观念的女性。在她身边,这些女性不用感到羞耻,不怕被看见,可以大声讨论面对生育时的困境、焦虑。
在接诊的大部分时间里,陈素文会安静地听完这些女性们的倾诉,仔细地给出治疗意见,然后温柔坚定地告诉她们:“不着急,慢慢来。”
在计划生育科这艘小小的避难船上,陈素文发现,随着教育、生育政策、人口的变化,来到船上的女性们的想法、年龄、诉求也都在发生变化——
更年轻的女孩来找她做人流手术,更年长的女性来找她“保胎”,流产手术越来越复杂、患有各种并发症的女性越来越多,而希望“上节育环”的女性,也随着政策开放重新走进了诊室。

这几年,计划生育科的工作重心也发生了变化,从“人流”转成了“保胎”。陈素文也感到,相伴三十年的“计划生育”这个词的意义,变得不同了。它不再是具有时代色彩的特定名词,而是更接近词语的本义:“该生的时候要优生优育,同时也要选择一个正确的、合适的生育间隔。”
如今,越来越多的女性更加迫切地想将生育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。陈素文总是在想,或许“计划生育科”,也是时候换种称呼了。
二胎政策后,计划生育科的已婚女性
陈素文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头发花白的母亲了。
3月底的北京,正值初春。下午的阳光温暖、明亮,斜斜地透过半透明的粉色窗帘,穿过这位母亲的发丝,洒在陈素文面前一叠叠病历本和诊疗单上。
陈素文隔着口罩向这位母亲打招呼,询问道:“女儿怎么样?”
“8周了。”这位母亲回答道,眼角的鱼尾纹流出笑意。
陈素文低下头,继续看着诊疗单。她的患者并非这位头发花白的母亲,而是她未到场的女儿——一位年轻孕妇。这位准妈妈经历过两次胎停,两个月前终于怀上了孩子,却又因此焦虑,不敢单独去陈素文的诊室看病。只能让由母亲代替她挂号,向陈素文递检查结果。
她告诉这位母亲,让女儿多补血,再来做检查,并叮嘱她向女儿传达,不要害怕,她会一直陪着她们,直到孩子出生。
陈素文本就擅长治疗不孕不育症。2020年“三孩政策”出台,许多因为胎停而需要重复做人流手术的已婚妇女,开始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她的诊室中。
这些女性大多已经过了35岁,最年长的有44岁,甚至有的女性已经育有一个孩子。她们几乎都属于高危产妇——除了年龄增长带来的亚健康问题和慢性疾病外,她们中几乎一半的人在初产时会选择剖腹产。剖腹产造成的瘢痕子宫,让这些女性重新怀孕的能力下降,怀孕位置风险度增加,让原本“简单”的日间手术变成了“高危流产”。
但这并不能让她们放弃。陈素文的诊室里,到访过太多重复胎停流产的已婚女性。她记得,最多的一次,有一位病人经历了6次流产,仍然希望能“再试一次”。
一次次的失败后,每位女性出现的症状都不近相同,但都会在诊疗结束时问陈素文:“我什么时候能开始再次备孕?”听到她的回答是至少3个月之后,就算隔着厚厚的N95口罩,这些女性们也无法掩饰脸上的失望。
焦虑,在计划生育科的诊室里,是陈素文和已婚女性的共同“敌人”。
除了重复流产和手术复杂度增加外,来问诊的女性年龄也开始两极分化——越来越年轻的未婚女性意外怀孕,排着队来找陈素文做人流手术:“二十年前,我接诊的最小人流患者是14岁,但这几年,我甚至接诊过11岁的。”
而越来越“高龄”的、甚至患有慢性疾病的产妇反而开始备孕、胎停、寻求“保胎术”,中间的年龄“断层”越来越大。
不仅在陈素文的科室,在北京另一家妇科医院的人流室里,20出头的年轻女孩们排着队,等着人流手术;而另一边的生殖中心里,50多岁的夫妇们,仍然在尝试做试管婴儿,努力乘上末班车,“再生一个”。
在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分会第六届主任委员程利南眼中,这与经济压力密不可分:“35~40岁的夫妻,家庭经济稳定了,这时候可能会再想生一个孩子。但多为独生子女的她们,上有四个老人,工作压力大,怎么会想多生孩子呢?”
即便越来越多的已婚妇女容易胎停,导致不得不人工流产,但很大一部分选择选择人工流产的已婚女性,仍然是因为“不想要孩子”。陈素文接诊过许多这样的女性,大多因为避孕失败或无效避孕而怀上了意料之外的孩子。
因此,已婚夫妇缺乏相应的性教育,在生育政策宽松的当下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议题。
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,2010-2014年,全球每年有超过5600万例人工流产手术,其中73%为已婚妇女。《2006年~2016年中国生育状况报告》提出,两次生育后的人工流产风险增加,意味着生育2孩后女性的避孕需求未能得到满足。
当陈素文问起这些已婚女性用什么方式避孕时,其中一位回答说,是体外避孕。
陈素文非常直接地说:“你自己也知道,这不能称之为避孕,”她皱起眉头,“根本不安全。”
这位年轻的已婚女性沉默了一会儿,问她:“什么样的人流方式能不伤子宫?”陈素文直截了当地回答:“生下来最不伤子宫。”
这位“北漂”女性,已经结婚并育有一个孩子。在这之前,她也曾做过一次人流手术。忙碌的生活和工作让她无力再去抚养第二个孩子,于是决定流产。
她问陈素文能不能“药流”,陈素文告诉她,因某些原因医院暂时没有提供“药流”了。这种方式效率没有人们期待的那么高,“流不干净”,容易引起并发症。“我们经常收治外院药流不全的患者,”陈素文说。
她听罢,思考了一会儿,与陈素文约了下周的手术时间,反复确认“到时候一定是陈主任做手术”后,才放心地离开诊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