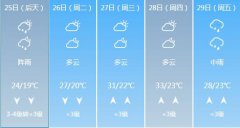母亲河,她有怎样的前世今生?
发布时间:2023-03-06 02:20来源: 未知母亲河,她有怎样的前世今生?
冬阳下的原野,恬适怡人:水洗过般的瓦块云飘过一拨又一拨,被人追赶着似的往前跑;云脚下,是一棵挨一棵合抱粗的梨树;而梨树丛中,掩映着一排排崭新的农家小楼——这里属安徽省砀山县的良梨镇,以盛产皮薄多汁、入口酥化的砀山梨著称。
步入梨树园,梨农们正埋头剪枝压枝、挖沟施肥。听说是从京城来的记者,一位大婶乐呵呵地说:“闺女,你应该过3个月再来。那时候,百万亩梨花都开了,美着呢!全国各地游客都往这儿跑呢。”
很难想象,记者置身的所在,竟是两百年前的黄河河道。
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。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”“泛彼柏舟,在彼中河”“河水洋洋,北流活活”……《诗经》中的“河”,指的就是我们的母亲河——黄河。与后世对黄河的认知不同,那时“河水清且涟漪”,一派悠然。然而,自《汉书》起,“河”开始多了另外一个名号“黄河”,泥沙成了河的主角,后代诗词对黄河的描写也变为刘禹锡笔下的“九曲黄河万里沙,浪淘风簸自天涯”,李白吟诵的“黄河西来决昆仑,咆哮万里触龙门。波滔天,尧咨嗟”……
“虎可搏,河难凭”,文辞之变的背后,是黄河带给人们的深深恐惧。因气候变迁、人类活动影响、流经黄土高原,让这条浩荡大河的泥沙含量居世界河流之冠。“黄河斗水,泥居其七。”千百年来泥沙淤积不断抬高下游河床,而两岸堤防也只能随之加高,黄河成为“地上悬河”。
“善淤”的黄河,越来越桀骜不驯,“善决”“善徙”导致水患频仍。据统计,从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,2500多年间,黄河下游决口1590余次,改道26次。“三年两决口,百年一改道”并非虚言。
决口改道,给两岸民众带来深重灾难。历史上的黄河洪水曾北抵天津,南达江淮,范围波及冀、鲁、豫、苏、皖五省。闻名遐迩的古都开封就曾6次被淹,层层淤泥,将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繁华湮没于黄沙之下。“道光二十三,洪水涨上天。冲走太阳渡,捎带万锦滩。”时至今日,河南省陕州区一带仍流传的这则民谣,记录了1843年洪水泛滥印刻在当地百姓心中的噩梦。
翻开黄河历次改道图,可以看到,在南宋建炎二年(公元1128年)之前,黄河大都在现行河道以北地区迁徙,注入渤海。而这一年,开封守将杜充为抵御金兵,在滑州李固渡扒堤决口“以水当兵”,导致黄河从此向南摆动改道,袭夺淮河水系,流入黄海。自此,决口和改道次数激增,令“走千走万,不如淮河两岸”的胜景不再,留下无数“江河横溢,人或为鱼鳖”的人间悲剧。
清咸丰五年(公元1855年),黄河在河南省兰考县东坝头附近再次决口,也再次改道,北流汇入渤海。从此,结束了700多年由淮入海的历史,留下一条蜿蜒于豫鲁皖苏四省交界之地的“明清黄河故道”。记者寻访母亲河来到的第一站——安徽省砀山县良梨镇,就系“明清黄河故道”。
离开良梨镇,记者来到山东省利津县盐窝镇。这里离现今的黄河入海口已不远。
“小时候,一发大水,就漫过河堤,人得赶紧转移,庄稼泡在水里。”利津县盐窝镇后左村党支部书记李美玲在黄河滩区长大,她告诉记者,“这些年,河堤不断加固,河道越来越深。前两年那么大的洪水,也没淹上岸。”
李美玲说的大洪水,是2021年秋季黄河中下游遭遇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秋汛——7轮秋雨连番登场,黄河干流9天内出现3次编号洪水,下游河道4000立方米每秒以上大流量洪水过程持续近30天……在如此严峻形势下,黄河防汛取得了“不伤亡、不漫滩、不跑坝”的成绩。
黄河故道的沧桑变迁,是新中国治理黄河的一个缩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