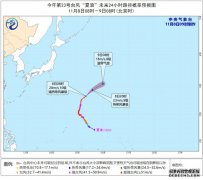中国历史上诗话最多的一朝
发布时间:2023-11-07 00:12来源: 未知清代诗话的数量为历代诗话之最,而清诗话中,又以道光一朝诗话体量最大。《清诗话全编》中,《道光期》诗话收录至九十一种,虽种类不及《乾隆期》的一百零三种,但体量较之乾隆期为大。盖由道光一朝,虽是清代由盛转衰的转折,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开始,但内部政治格局还相对稳定,文化政策也较为宽松。因之文人著书立说的热情较高,而留存后世书籍数量也大。如此,今天我们能够搜集到的道光诗话,数量自然也多了。
但更重要的原因应是道光期诗话本身的特色。诗话一体至道光朝,其编撰方式更为随意自由,以至于文人得以随写随记,不加拣择地随记随编,这导致了诗话的体量增大,也是道光诗话种类较之乾隆少了逾十种,但体量却比之乾隆诗话大了很多的缘故。最为显著的例子,有康发祥的《伯山诗话》,其“随到随刊”,亦不复诠次,竟至前集之下又有后集、续集、再续集、三续集、四续集之刻;潘焕龙之《卧园诗话》初刻四卷之后,又补编三卷、续编三卷。这种随记随编的方式也决定了其中所录的内容亦甚随意,多日常所见、兴到之语,甚或剿袭故书的读书笔记。这倒与诗话一体的起源——《六一诗话》的“以资闲谈”的旨归是一致的。
更有甚者。诗话“以资闲谈”的旨归,所记还限于诗人诗事,然道光诗话所记,则颇似有与诗无关者。《卧园诗话》中,甚有“话诗必泥诗,定非知诗话”之说,即认为诗话之作,并不一定要与记诗、论诗有关。故其诗话中,多有似全无与诗人、诗话相关者,如记古人敬惜残纸剩笺、考清之“折子”与宋之“札子”“帖黄”等;其他诗话中,亦间有这种情况,《橡坪诗话》记有名赵公权者九十而清健不衰,盖因读《论语》中学得三不:不多食、食不言、寝不语,事涉养生,不关诗学;又如《春草堂诗话》记前辈以《列女传》不当载蔡文姬辈的迂腐言论,乃以《列女传》为《烈女传》;《海粟诗话》记“杜拾遗庙”被村夫修缮为“杜十姨庙”,又做女像以配刘伶,足发一噱,皆或关社会风俗,与诗人诗事也并无直接联系。再联系《卧园诗话》中记载潘焕龙的朋友丁杰谈诗话不必泥诗之语,可知道光之诗话实有超出记诗人诗事“以资闲谈”的旨归:“就中有即诗为话者,有离诗为话者,有不以话为话者,率皆位置得宜,剪裁合度。如正说诗时,忽间以古今事,实推波助澜,旁见侧出,似是闲话,实非闲话,弥觉生趣盎然。”诗话所记,不必有一定之限,不论古今,不论体裁,亦不论是否与诗有直接关联,但有一点,它不是严肃的学术考证或一本正经的高头讲章,而讲究“生趣盎然”,我们平时讲究的“诗意的生活”或是“生活中的诗意”,不也正在“生趣盎然”四字么!如此,道光诗话终究还是与诗有关:它记载了诗人雅士们诗意生活的一切。如此,诗话之体至道光一朝,被赋予了新的旨归:即诗人雅士诗意生活的多元记录。
二
正因如此,道光诗话较之前代诗话的特点,即在它涉及领域更广、记载范围更宽,可反映诗人雅士们日常生活的多个面向。除谈诗论艺之语、诗人之佳作佳句外,社会百态,乃至风俗游戏,无所不有,读之颇可窥清人诗情画意生活之一斑。比如诗话中提到时人在酒席中经常玩的一种与诗有关的酒令游戏:
酒令近人多摘唐句作签,注明座中人举动有合诗意者,即飞一觥,如“人面不知何处去”,注大胡(大胡子)者饮;“几度呼童扫不开”,注近觑(近视)者饮。(《橡坪诗话》卷六)
清代诗人如何劝酒、行酒令?这条珍贵的材料给予了我们一个有趣的答案,原来酒席间决定清代诗人喝不喝酒,是用抽诗签的方式。座中人的行貌有与抽中诗句意思相关的,比如大胡子将面部遮了个干净,正是“人面不知何处去”,须饮酒;“几度呼童扫不开”,扫的是花影,而“花影”亦可为“眼花之影”,故近视眼者正符合句意,亦须饮酒。
涉游戏者尚有“诗谜”,猜字谜为中国传统游戏,而清代诗人之字谜,亦与诗有关,如《橡枰诗话》卷四载字谜云“清新庾开府,俊逸鲍参军”,这是杜甫《春日忆李白》的诗句,而这两句又是以南朝两位大诗人比李白,故谜底是“比白”即一个“皆”字,趣味盎然。《橡坪诗话》中载清人诗歌游戏最多,除“诗谜”外,尚有“诗牌”一种,屡见于该诗话。如说长洲学士顾元熙之《兰修馆丛集》内有《碎锦集》用诗牌集字成者;又载药根和尚的诗牌成句“雨窗话鬼灯先暗,酒市论仇剑忽鸣”等等。考诗牌游戏,即用作诗之常用字作为牌面,游戏者以一定规则,将自己手头的牌凑成诗篇或诗句,以成诗的迟速与诗篇的优劣作为胜负依据。玩法也是五花八门,简单的如抽签一般,游戏者将手头抽到的牌凑成诗篇;复杂者则限韵、限体裁、限题材者皆有。更有竞技性强的玩法,犹如今人之打麻将:游戏者通过各自的摸牌、打牌、吃牌等,拿到自己想要的字牌,从而凑出自己想要的佳句佳篇。清代诗人推杯换盏、消遣娱乐之际,也是如此的诗情画意!
明 杜堇《玩古图》
此其小者。其中又有诗人对时事的评价与记录。众所周知,中国近代走向衰落,为西方列强侵略的直接导火索就是鸦片,而鸦片之逐渐泛滥,成为毒害中华民族精神的毒药,正在道光前后。诗话中亦有对鸦片烟毒害国人心智的批评:
哀哉,夫鸩毒害人,见之者必变色疾趋,避之惟恐不速,间有服毒自戕,其命非迫于饥寒,即罹于法网,无生人之乐,遂视死如归。彼食鸦片烟者,明知耗财伤命,甘心不顾,亦何为哉!(《春草堂诗话》卷十四)
将鸦片烟与鸩毒相比,言鸩毒之害,更为明显,故非欲自戕者,避之不及。但鸦片却使人心甘情愿地被毒害,可谓为祸甚于一般的毒药。这也使我们知道,道光鸦片泛滥之初,当时的知识阶层对其毒害民众的特性,还是有一定的认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