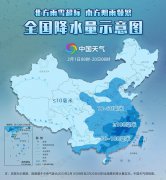张之洞最初计划将铁厂设在广州河南凤凰岗
发布时间:2023-03-09 01:40来源: 未知
未有铁矿,先购机器
学界谈张之洞在广东办洋务,多提到1885年设立矿政局(矿务局)一事,以此作为他的业绩之一。矿政局的设立,是听从粤商何献墀的建议,但其人员构成却令人费解。矿政局有两个总办,一是李蕊,一个彭懋谦。这两位都属于非常传统的读书人,其知识结构、历练并不适合这个岗位。
李蕊(1822-1886),湖南祁阳人,字仙舟,号奎楼,1869年投笔从戎,加入平江营,后肆力科举,中进士点翰林,1879年以试用道分发广东,数年间无所事事,遂编撰60万言的《兵镜类编》一部。1883年曾国荃督粤,以同乡关系委以重任,任善后局总办。此次出任矿政局总办,可以肯定是出于同乡彭玉麟的力荐。张之洞曾写信给堂兄张之万,抱怨彭玉麟在广东,“要差要缺,几欲无人非湘人而后已。”另一个总办彭懋谦(1833-1905),字小皋,陕西省石泉县人,由增贡生报捐同知,同治九年(1870)中举人,次年联捷成进士,授工部主事,改捐道员指分广东,光绪八年署惠潮嘉道,十年四月署督粮道。历任广东报销、厘务、善后、矿政等局总办。这两个总办可以说是传统的学者、循吏,操守都很廉洁,但实在不适合安排在这个岗位上。这个位置,需要的是懂一些地质学、能与欧美机器采矿业界联络、吃苦耐劳的开拓型人才。
事实证明,矿政局的设立,对张之洞找矿并无帮助,他实际是依赖广东水师提督方耀帮忙探矿。方耀经常在惠州各属“剿匪”,本人对开矿极有兴趣,组织了一些商人在各地探矿。1886年1月3日,方耀电告张之洞:“惠属矿务,经派人协商,分往查探,兹据覆,河源之大叶山等处,铁苗甚旺,归、博、长、永各属亦多铁矿兼有五金矿山。现购有机汽及造成小炉,拟运赴各该处先行试探、试炼,一面会府行县查照,仍俟倾煎成质,察看情形若何,再行督商妥议,具报开办。”(《广州大典》总第344册)方耀在惠属探矿多年,未见有何显著成效。作为军事领导人,方耀将探矿当作可有可无之事,只是让商人自己探查,没有组织一个班子专门负责,惠州知府、各属知县实际也不闻不问。张之洞听信了方耀的“情报”,认为广东总是能找到铁矿,在没有探明地点、储量、品位的时候,下决心从英国订购大型炼铁设备,几近儿戏。
直到1899年冬,铁厂设备已付定金,张之洞才意识到要找惠州知府落实铁矿坐落何处。11月初,他急电惠州知府督责:“该府设局开矿日久,未据详报,闻煤、铁、铜、锡各矿均有,究竟何处现开何矿、何处所得最多、何处矿质最良、多者能出若干,其转运煤、铁,何处水口最为近海、运脚几何、应以何处为聚集之所,速饬归善、河源、永安、龙川四县令即日亲往确勘。”(《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》第二辑第8册)意想不到的是,新任薛知府回电,方耀并无设立矿务专门机构,前任知府只是一纸塞责:“惠府矿务,方提督并未开局,各商亦未领照开办,何处、何矿丰旺,必须开探方知。前李守禀呈山场清折,各县均未查复。”前任知府李璲在张之洞、方耀双重压力下,开列过惠属各处矿场地名,但各县知县并无亲到现场履勘,也久无回复。商人何献墀开发大屿山银铅矿不顺利,张之洞认为是商人不懂开矿的结果,开矿必须“官为经理”。从惠州知府的回复,我们可以清楚看到“官为经理”的结果。
洪钧的反对意见
张之洞也明白探矿需要西洋矿师协助,只是观念陈腐,招揽不得法。中法战争印证了他头脑中固有“重赏之下必有勇夫”的观念,但在招揽西方采矿工程师方面,仍持有这种旧观念,并不是都可行。
1889年4月9日,已经准备订购设备,他到这个时候才想起请刘瑞芬在英国“觅上等矿师”。刘瑞芬千辛万苦,找到一个愿意来中国的矿师,到9月份又起变故,说是“因家务不能来”。(《广州大典》总第343册)12日,张之洞致电洪钧:“琼、惠等府现兴矿工,请代订精于铜铁矿师二人,务须上等,议定月薪、年限及盘费,能速订速来尤感。”也即他已准备下单订购炼铁设备,但采矿工程师尚未物色到,急急忙忙,托完刘瑞芬,觉得不保险,又托洪钧帮助物色。
驻德公使洪钧有自己的见解,不会对张之洞言听计从。从来往电报看,洪钧对近代矿业、工业的了解,比张之洞高明许多。对寻找上等矿师问题,洪钧回答:“上等矿师皆享月俸,非有经久重利,未肯远适。”欧洲上等采矿工程师均有优厚待遇,除非确信能得到长期的高回报,不会随便到远东来。
需要补充的是,欧洲人多不能适应广东炎热气候,加上热带传染性不时流行,当日两广地区的传教士及其亲属死亡率、染病率极高。为了高薪而不幸送命,或落个终生残疾,得不偿失,这是“重赏之下必有勇夫”很难行得通的重要原因。这年秋天洪钧帮张之洞在德国找到的副矿师“行至新加坡身故”,就是例子。
对广东开设炼铁厂的计划,洪钧毫不客气地一口反对:“粤中铜、锡矿可开,铁矿不可开。购机设厂,需款甚钜,尚请熟筹。”(《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》第二辑第64册)洪钧对广东矿藏情况了解较深,坚决认定粤中“铁矿不可开”。此处“不可开”之意,是缺乏大型富铁矿,小型的贫铁矿不能适应需求。洪钧进一步警告说,购买机器设备设立炼铁厂,总投资金额甚钜,要张之洞慎重考虑再说,实际上是否定了在广东开设炼铁厂的计划。广东的富铁矿,要到1939年,侵华日军在海南石碌发现。即使当时张之洞手下找到石碌铁矿,从海南腹地矿区到广州的运费也不低。
英国方面宣布涨价后,张之洞曾打算转向德国订购,八月廿三日致电洪钧:“请定镕铁大炉二座,日出生铁一百吨,并炼熟铁、炼钢各炉,压板、抽条兼制铁路各机器,一切配全,能拆开分运,经行山路至内地者尤好,价若干、几月造成、需用洋匠几人、薪工若干,望悉查示。款已筹备,此系详筹必办之事,务恳速议见复。”(《近代史所藏清人稿本抄本》第二辑第8册)后因刘瑞芬与英厂再次谈妥,从德国引进设备的计划没有再提。
英厂涨价
张之洞洽购炼铁设备,与纱厂、枪炮厂一样,都由驻英公使刘瑞芬具体操办,张之洞坐镇广州,用电报发纵指示,刘瑞芬则不辞辛苦,与厂家作唇燥舌焦的艰苦谈判。不过,由于汇丰银行汇兑定金时出现延误,英国厂家重新报价时突然加价。
1889年4月9日,张之洞同时致电刘瑞芬、洪钧:“粤多铁矿,质美价廉,惟开采煎炼未得法,故销路甚隘。请查开铁矿机器全副需价若干,将生铁炼熟铁,将铁炼钢,兼制造钢板、钢条、铁板、铁条及洋铁针并一切通用钢铁料件需用机器,约价几何。粤拟设炼铁厂,请详询示复。”
刘瑞芬凡张之洞托办之事,二话不说,先做了再说,不持异议,即或有疑问,也是以温和之语出之。洪钧却不会稍加辞色,对张之洞的做法,有时直接否定:“开矿机价自十万马至五六十万不等,须相地而施;炼铁机器亦须知日炼若干,无从悬揣,总以矿师测验为首务。现正物色良师,未敢草率报命。”(《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丛书》第二辑第8册)“无从悬揣”四字,体现了洪钧的科学精神。
就在奉调湖广前一天(8月7日),张之洞发电刘瑞芬催督:“铁机请速定,尚未奉示复,盼切之至。立等具奏,即定迅复。”原来,开设铁厂的资金,是向广东全省“官吏绅商”勒捐而来,必须尽早向朝廷出奏成为定案,若一直未能奉旨允准,这笔钱就没有“合法”身份。张之洞自吹自擂,总说自己在粤省筹款“取之中饱”,兵工厂投资、铁厂投资是全省各级官员“凑捐”,说“取之中饱”有点不公平,贪官对这点勒捐经费当然无所谓,苦的是真正的清官。所谓“绅商”,笔者猜测主要是官商身份的盐商之类。
8月14日,刘瑞芬奉命与英厂谛塞德公司(Tees-side Engine Company of Middlesbrough,张之洞电报档作“谐塞德”,可能是译电错误))签订“镕铁大炉”合同。9月5日,张之洞收到刘瑞芬回电:“炼铁机炉,该厂因过期多日未付定银,现工料各价腾涨,前议已作罢论。”(《近代史所藏清人稿本抄本》第二辑第65册)当张之洞要求与该厂再议时,9月6日刘瑞芬答复“此时颇费唇舌,业与该厂说绝,现难再议”。
英厂突然涨价,刘瑞芬与之理论,几乎翻脸。张之洞铁厂专款筹集告成,势难中止。最终,经刘瑞芬与英厂再次谈判,仍以原价成交,签订合同。突然涨价以及刘瑞芬所言“业与该厂说绝”,背后有无李瀚章操纵,殊难判断。李瀚章无意把炼铁设备留在广东,并不表明他反对兴办近代工业,而是深知张之洞此举鲁莽冒失,铁厂投资是个“无底洞”。
9月,张之洞奏上《筹设炼铁厂折》,报告朝廷:从英国公司引进炼铁设备连同配件等,总价款八万三千五百镑(折合白银约39.5万两),厂址“择定于省城珠江南岸之凤凰岗地方,水运便利,地势平广”。此地原是广州八旗水师营把守的凤凰岗炮台所在,两次鸦片战争中都没有发挥什么作用,“水运便利”倒是实情,后来日商在此建成大阪码头与仓库。
学界谈张之洞在广东办洋务,多提到1885年设立矿政局(矿务局)一事,以此作为他的业绩之一。矿政局的设立,是听从粤商何献墀的建议,但其人员构成却令人费解。矿政局有两个总办,一是李蕊,一个彭懋谦。这两位都属于非常传统的读书人,其知识结构、历练并不适合这个岗位。
李蕊(1822-1886),湖南祁阳人,字仙舟,号奎楼,1869年投笔从戎,加入平江营,后肆力科举,中进士点翰林,1879年以试用道分发广东,数年间无所事事,遂编撰60万言的《兵镜类编》一部。1883年曾国荃督粤,以同乡关系委以重任,任善后局总办。此次出任矿政局总办,可以肯定是出于同乡彭玉麟的力荐。张之洞曾写信给堂兄张之万,抱怨彭玉麟在广东,“要差要缺,几欲无人非湘人而后已。”另一个总办彭懋谦(1833-1905),字小皋,陕西省石泉县人,由增贡生报捐同知,同治九年(1870)中举人,次年联捷成进士,授工部主事,改捐道员指分广东,光绪八年署惠潮嘉道,十年四月署督粮道。历任广东报销、厘务、善后、矿政等局总办。这两个总办可以说是传统的学者、循吏,操守都很廉洁,但实在不适合安排在这个岗位上。这个位置,需要的是懂一些地质学、能与欧美机器采矿业界联络、吃苦耐劳的开拓型人才。
事实证明,矿政局的设立,对张之洞找矿并无帮助,他实际是依赖广东水师提督方耀帮忙探矿。方耀经常在惠州各属“剿匪”,本人对开矿极有兴趣,组织了一些商人在各地探矿。1886年1月3日,方耀电告张之洞:“惠属矿务,经派人协商,分往查探,兹据覆,河源之大叶山等处,铁苗甚旺,归、博、长、永各属亦多铁矿兼有五金矿山。现购有机汽及造成小炉,拟运赴各该处先行试探、试炼,一面会府行县查照,仍俟倾煎成质,察看情形若何,再行督商妥议,具报开办。”(《广州大典》总第344册)方耀在惠属探矿多年,未见有何显著成效。作为军事领导人,方耀将探矿当作可有可无之事,只是让商人自己探查,没有组织一个班子专门负责,惠州知府、各属知县实际也不闻不问。张之洞听信了方耀的“情报”,认为广东总是能找到铁矿,在没有探明地点、储量、品位的时候,下决心从英国订购大型炼铁设备,几近儿戏。
直到1899年冬,铁厂设备已付定金,张之洞才意识到要找惠州知府落实铁矿坐落何处。11月初,他急电惠州知府督责:“该府设局开矿日久,未据详报,闻煤、铁、铜、锡各矿均有,究竟何处现开何矿、何处所得最多、何处矿质最良、多者能出若干,其转运煤、铁,何处水口最为近海、运脚几何、应以何处为聚集之所,速饬归善、河源、永安、龙川四县令即日亲往确勘。”(《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》第二辑第8册)意想不到的是,新任薛知府回电,方耀并无设立矿务专门机构,前任知府只是一纸塞责:“惠府矿务,方提督并未开局,各商亦未领照开办,何处、何矿丰旺,必须开探方知。前李守禀呈山场清折,各县均未查复。”前任知府李璲在张之洞、方耀双重压力下,开列过惠属各处矿场地名,但各县知县并无亲到现场履勘,也久无回复。商人何献墀开发大屿山银铅矿不顺利,张之洞认为是商人不懂开矿的结果,开矿必须“官为经理”。从惠州知府的回复,我们可以清楚看到“官为经理”的结果。
洪钧的反对意见
张之洞也明白探矿需要西洋矿师协助,只是观念陈腐,招揽不得法。中法战争印证了他头脑中固有“重赏之下必有勇夫”的观念,但在招揽西方采矿工程师方面,仍持有这种旧观念,并不是都可行。
1889年4月9日,已经准备订购设备,他到这个时候才想起请刘瑞芬在英国“觅上等矿师”。刘瑞芬千辛万苦,找到一个愿意来中国的矿师,到9月份又起变故,说是“因家务不能来”。(《广州大典》总第343册)12日,张之洞致电洪钧:“琼、惠等府现兴矿工,请代订精于铜铁矿师二人,务须上等,议定月薪、年限及盘费,能速订速来尤感。”也即他已准备下单订购炼铁设备,但采矿工程师尚未物色到,急急忙忙,托完刘瑞芬,觉得不保险,又托洪钧帮助物色。
驻德公使洪钧有自己的见解,不会对张之洞言听计从。从来往电报看,洪钧对近代矿业、工业的了解,比张之洞高明许多。对寻找上等矿师问题,洪钧回答:“上等矿师皆享月俸,非有经久重利,未肯远适。”欧洲上等采矿工程师均有优厚待遇,除非确信能得到长期的高回报,不会随便到远东来。
需要补充的是,欧洲人多不能适应广东炎热气候,加上热带传染性不时流行,当日两广地区的传教士及其亲属死亡率、染病率极高。为了高薪而不幸送命,或落个终生残疾,得不偿失,这是“重赏之下必有勇夫”很难行得通的重要原因。这年秋天洪钧帮张之洞在德国找到的副矿师“行至新加坡身故”,就是例子。
对广东开设炼铁厂的计划,洪钧毫不客气地一口反对:“粤中铜、锡矿可开,铁矿不可开。购机设厂,需款甚钜,尚请熟筹。”(《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》第二辑第64册)洪钧对广东矿藏情况了解较深,坚决认定粤中“铁矿不可开”。此处“不可开”之意,是缺乏大型富铁矿,小型的贫铁矿不能适应需求。洪钧进一步警告说,购买机器设备设立炼铁厂,总投资金额甚钜,要张之洞慎重考虑再说,实际上是否定了在广东开设炼铁厂的计划。广东的富铁矿,要到1939年,侵华日军在海南石碌发现。即使当时张之洞手下找到石碌铁矿,从海南腹地矿区到广州的运费也不低。
英国方面宣布涨价后,张之洞曾打算转向德国订购,八月廿三日致电洪钧:“请定镕铁大炉二座,日出生铁一百吨,并炼熟铁、炼钢各炉,压板、抽条兼制铁路各机器,一切配全,能拆开分运,经行山路至内地者尤好,价若干、几月造成、需用洋匠几人、薪工若干,望悉查示。款已筹备,此系详筹必办之事,务恳速议见复。”(《近代史所藏清人稿本抄本》第二辑第8册)后因刘瑞芬与英厂再次谈妥,从德国引进设备的计划没有再提。
英厂涨价
张之洞洽购炼铁设备,与纱厂、枪炮厂一样,都由驻英公使刘瑞芬具体操办,张之洞坐镇广州,用电报发纵指示,刘瑞芬则不辞辛苦,与厂家作唇燥舌焦的艰苦谈判。不过,由于汇丰银行汇兑定金时出现延误,英国厂家重新报价时突然加价。
1889年4月9日,张之洞同时致电刘瑞芬、洪钧:“粤多铁矿,质美价廉,惟开采煎炼未得法,故销路甚隘。请查开铁矿机器全副需价若干,将生铁炼熟铁,将铁炼钢,兼制造钢板、钢条、铁板、铁条及洋铁针并一切通用钢铁料件需用机器,约价几何。粤拟设炼铁厂,请详询示复。”
刘瑞芬凡张之洞托办之事,二话不说,先做了再说,不持异议,即或有疑问,也是以温和之语出之。洪钧却不会稍加辞色,对张之洞的做法,有时直接否定:“开矿机价自十万马至五六十万不等,须相地而施;炼铁机器亦须知日炼若干,无从悬揣,总以矿师测验为首务。现正物色良师,未敢草率报命。”(《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丛书》第二辑第8册)“无从悬揣”四字,体现了洪钧的科学精神。
就在奉调湖广前一天(8月7日),张之洞发电刘瑞芬催督:“铁机请速定,尚未奉示复,盼切之至。立等具奏,即定迅复。”原来,开设铁厂的资金,是向广东全省“官吏绅商”勒捐而来,必须尽早向朝廷出奏成为定案,若一直未能奉旨允准,这笔钱就没有“合法”身份。张之洞自吹自擂,总说自己在粤省筹款“取之中饱”,兵工厂投资、铁厂投资是全省各级官员“凑捐”,说“取之中饱”有点不公平,贪官对这点勒捐经费当然无所谓,苦的是真正的清官。所谓“绅商”,笔者猜测主要是官商身份的盐商之类。
8月14日,刘瑞芬奉命与英厂谛塞德公司(Tees-side Engine Company of Middlesbrough,张之洞电报档作“谐塞德”,可能是译电错误))签订“镕铁大炉”合同。9月5日,张之洞收到刘瑞芬回电:“炼铁机炉,该厂因过期多日未付定银,现工料各价腾涨,前议已作罢论。”(《近代史所藏清人稿本抄本》第二辑第65册)当张之洞要求与该厂再议时,9月6日刘瑞芬答复“此时颇费唇舌,业与该厂说绝,现难再议”。
英厂突然涨价,刘瑞芬与之理论,几乎翻脸。张之洞铁厂专款筹集告成,势难中止。最终,经刘瑞芬与英厂再次谈判,仍以原价成交,签订合同。突然涨价以及刘瑞芬所言“业与该厂说绝”,背后有无李瀚章操纵,殊难判断。李瀚章无意把炼铁设备留在广东,并不表明他反对兴办近代工业,而是深知张之洞此举鲁莽冒失,铁厂投资是个“无底洞”。
9月,张之洞奏上《筹设炼铁厂折》,报告朝廷:从英国公司引进炼铁设备连同配件等,总价款八万三千五百镑(折合白银约39.5万两),厂址“择定于省城珠江南岸之凤凰岗地方,水运便利,地势平广”。此地原是广州八旗水师营把守的凤凰岗炮台所在,两次鸦片战争中都没有发挥什么作用,“水运便利”倒是实情,后来日商在此建成大阪码头与仓库。